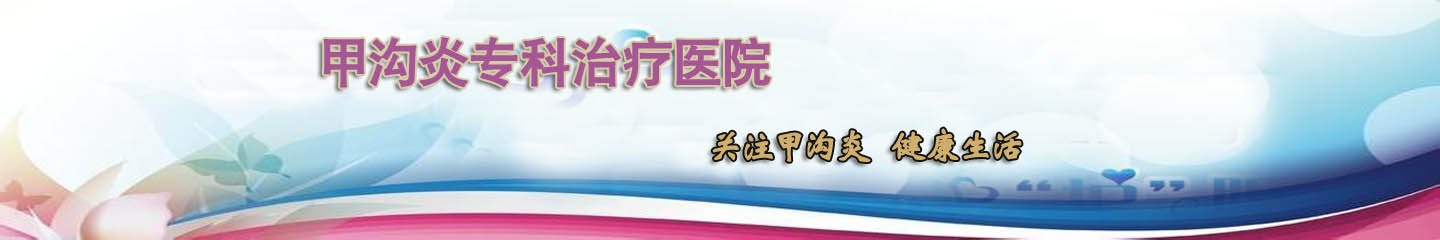闽南中医文化阿公阿嬷的偏方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分支,大多可以分为两部分,按顾城说的,一个是墙里的大观园,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中医也不例外,一部分是庙堂之内的正规军,一部分是江湖之中的绿林军,由学院派的“经方时方”和民间的“偏方验方”两者构成。
偏”即是与“正”相对,我们统称它们为“偏方”或者“验方”的概念,即是充满了古人开脑洞、小概率触发找到办法,并在历史长河中广泛施用于大样本临床患者得出的经验。例如灯芯草点灸可以治疗带状疱疹、螃蟹可以生肌敛疮、小葱头与生土豆捣烂外敷可治甲沟炎、茶叶渣存于空罐中待其糜烂可外用治疗烫伤及各种疮疡肿毒,等等等等,这些偏方验方属于常理逻辑不可推演的范畴,许多由目不识丁的劳动人民一代代口口相传,你知道便是知道,不知道你就开一个直径50公分的脑洞也是没办法知道,不讲道理。
偏方验方的使用,很多情况下仅有一、二个指征,甚至不需要依据中医理论进行辨证即可使用,时而有“偏方验方气死名医”、出其不意的效果,也会有“偏方验方方方不应”、如石沉海的尴尬。由于近代以来经历过的时局动荡、门户之见、使用材料的缺失或是难以获取、患者难以接受,许多民间的偏方验方因为疏于整理已无声遗失。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闽南中医里面的各种偏方验方,尤其是那些赤脚医生、裹脚阿婆的土办法,这些土办法与我而言宛如沧海遗珠,它们被妖魔化、边缘化的原因是疏于总结、疏于整理,更缺乏证据。当下的各种技术手段难以做到揭示它们的功效证据,但我们有必要以记录者的身份将其延续,随着时间推移该淘汰的将被淘汰,能生存的继续生存。
闽南中医体系地域特色很鲜明,各种当地青草药和食材的混搭是其一大特色,民间草药食疗氛围浓厚,从小到大耳濡目染,闽南人的意识被动植入了很多药膳配方,肯定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有这种记忆:儿时砂锅里飘出的香味,你闻了就知道是阿嬷在煲鸭汤,而且加了特别的配料,但是除了知道里面有一只鸭以外你什么都不晓得;发烧的时候迷迷糊糊被阿公半夜叫起来喝水,水咸咸怪怪的,你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开水,第二天醒来退烧了,也就扔掉了对昨晚那碗液体可有可无的好奇。
再大几岁,我们也知道了炖番鸭要加“四物”,鲫鱼汤要放当归,上火要泡“桑芽杭菊”,肠胃不好要小肠炖“四神”,消瘦盗汗可以吃“四脚蛇”,腰腿痠痛猪尾炖“一条根”,发烧去草埔里摘“天青地红”,感冒去天台割“风葱”,这些都是闽南地区口口相传、代代相述的,从缺医少药、物品匮乏的年代总结出来的生活结晶,也是我们培养优质后代的重要保证。对这些文化进行传承,比起煮碗敬天公、清明烧Iphone显然更尽一份孝道。
立冬补冬,是闽南人的重要习俗。虽然闽南的立冬没有刺骨的冬风,只有刹不住车的秋意,不过立冬日煲一锅番鸭四物汤也是千年不易的当季爆款,也可以更好地驱除闽南冬日的阴湿。一锅棕色的四物汤端上,带着浓浓的鸭肉香,伴着淡淡的药香,熊熊喝一口,活到九十九。“四物”由川芎、芍药、熟地、当归四味药组成,四物名由此而来。川芎行气,芍药、当归养血活血,熟地滋肾养阴,从来都是闽南女人的98号汽油。
闽地多湿气,芡实(又称“鸡头米”、“鸡头”等)这味药,能健脾祛湿、固肾止泻,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优势,在苏东坡的养生之道中,就强调吃芡实。鲜芡实或干芡实泡水后可直接嚼服,也可将其和莲子、茯苓、山药一起煮成四神汤,莲子健脾宁心,茯苓健脾利湿,山药平补三阴,四者具有健脾、利湿、补肾的功效,适合大部分人饮用。常熬夜、长痘痘、易嘴破、常便秘的人亦适合饮四神汤(可与瘦肉或者大小肠、猪肚等同炖)来健脾益气、祛湿建中,让消化系统稳定下来。
下面我另外列出部分最为常用也方便的食疗及偏方整理出来以飨众位,详细使用指征和方法可进
转载请注明:http://www.ddnhj.com/wadzz/1307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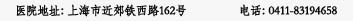
当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