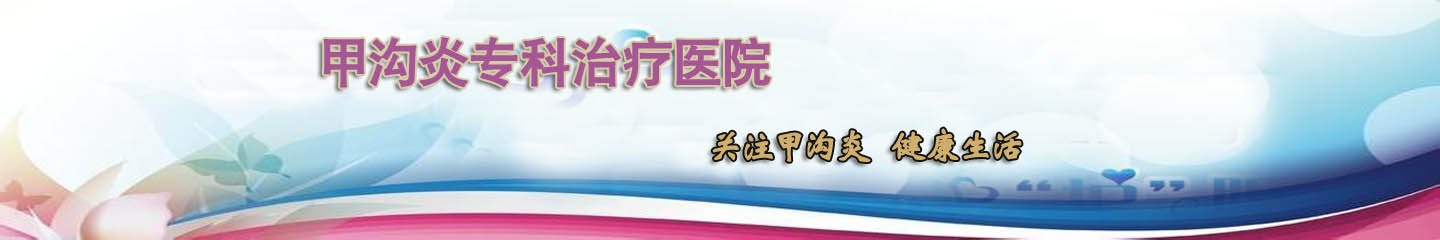雷勤风钱钟书的早期创作
作者供职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
引论
钱钟书(–)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出身世代书香之家,后来求学于国内外的一流学府。他从抗日战争(–)初期到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写出了他大部分的散文和小説作品,可以算是乱世中的作家。[i]他虽然后来偶尔还会作诗、写论文,但是他的文学生涯—就如不少同辈们一样—被中国内战的结果所割断。不过,在那十年之间,钱钟书为文学现代性做出了很多种惊人的贡献,有的至今还未被全面了解。
一大部分钱钟书的早期创作收入《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两本集子。在其中我们看到他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正在形成中。[ii]这些作品多半是在钱钟书从欧洲进修回国之后的战乱时代写的,而且它们对现代中国最乱轰轰的时期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当中国作家争先恐后地唿应“救亡文学”号召的时代中,钱钟书却出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其内的文章似乎多谈笔战,少谈抗战。到了抗战末期,他写了四篇短篇小説,其形式不使用流行的史诗体,反而更像家庭心理剧和奇幻讽刺小説。不过读者体会到,在他的散文中各篇的基本批评对象并不能只从它们的杂题本身(譬如:窗和门的不同喻意,或者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盲点等)看得出来。他的小説也不限于时事性。钱钟书的散文和短篇小説一样,不断地探索语言本身的各种局限和可能性,并显出这位以“批评之眼”观看一切的作家的独一无二的语言技能和独立知识精神。
幸亏,钱钟书并没有以哲学家的玄道或者道学家的专横姿态施展他的文学观,反而让读者通过他万变的机智语言,不断地有新的发现。的确,如下所述,这两部书浸透了一种“百科全书体”的讽刺风格,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被中断的重要脉络。至今,钱钟书的早期作品所引起的学术批评,远远少于《围城》(-)和《管锥编》(-)。[iii]因此,本篇的目的为重新评价《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
钱钟书的短篇小説和散文
关于《写在人生边上》,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説史》写过,“钱钟书仅以清淡的姿态出现,因此我们看到的,亦只是他那份迫人的才气与学问的一小部份而已。”关于《人兽鬼》他又说了,“钱钟书写的短篇小説太少,无法作一个全面的评价。但除了「上帝的梦」这有阿诺托尔?法郎士(AnatoleFrance)风格的轻浮寓言外,「人、兽、鬼」的其余作品—「灵感」、「猫」、「纪念」—对发展中的中国短篇小説传统,都各自有其不少贡献。”[iv]在我看来,钱钟书写在《围城》前的几篇作品所表现的作家姿态,可谓是知识贵族,因爲钱钟书不仅传承了中国的古典学术传统,也把它延伸到西方文学的广阔场域中。这些早期创作充满古今中外的文学和文化典故,而且—除了小説《纪念》以外—採取一个居高临下的讽刺风格,对知识分子特别齿冷。耿德华(EdwardGunn)曾经说钱钟书一针见血的讽刺、对人类的悲观态度,以及小説中的反英雄(antihero),象徵战时上海文坛的“反浪漫”(antiromantic)潮流,因爲他的小説很少提个人的自我肯定等主题,反而强调“自我欺骗所带来的个人失败。”[v]不过,钱钟书的早期创作也似乎并非以探讨个人心理为主要目标,而有意把个人和典範(types)当作语言游戏的焦点。重读《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能够让我们对钱钟书的世界观和文学风格有新的发现。在下面,我提出叁点。
辞海为家:文学世界主义
首先,这些文章表现出来的脾气、视野,以及表达能力,无疑都是一位四海爲家者的世界主义。钱钟书再叁地回到两个似乎狭窄的话题—文学与批评实践—但是他的探讨範围并不偏狭,因爲它的对象就是印象人生经歷的知能认识论。很多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知识分子,常常用他们对多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熟悉来使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界具体化,并在二分法式的比较下,左右逢源,从中得利。与此相比,钱钟书的文章搭起来了一个多面的语言宇宙,各种思想和説法被吸进他的轨道之后,有时往难以预料的方向再弹出来。
这个现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钱钟书的创作里多而广的文学与文化典故,亦是他的笔风的特点之一。譬如,在散文《论快乐》中,所罗门,马拉梅(Mallarmé),苏东坡,王丹麓,诺凡利斯(Novalis),罗登巴煦(Rodenbach),和白洛柯斯(B.H.Brockes)在一段话里并肩而立。这样的博学排场虽然令不少读者眼花撩乱,有的读者却给他的掉文舞墨扎了眼。譬如说,有一位西方传教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书,一定会令钱钟书好笑,因爲那位《围城》的书评人不耐烦地抱怨“作者不由自主地衒弄学问,就是説,提出既无用又离题的外文标语和谚语(如:德文,西班亚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令一般读者反胃。任何人查查词典也能做得到这事。”[vi]实事上,钱钟书的用典比较虽然多,但是既不简单又不是无意义的。
这种文学与文化典故在钱钟书的早期作品中出现帝更加稠密。这种写法把本来可能没有系谱关係的説法并列起来,因而不仅“打通”[vii]了其背后的思想,而且开拓了一场思想校场。该领域中,作者也不以某想法的国内外出处来假设想法的高下。这种作文的方法是钱钟书自成一家的“比较文学”。这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糅合,既是他的小説和散文的特点,后来也见于《管锥编》字句方面的基本结构逻辑。这种创作手法仿佛把两种脉络融合在一起:第一个是以极少的解説“结缔体素”来并列相关字句的中国古代注释传统,第二个是十七世纪欧洲文学的“巴洛克(baroque)风格”的逌然和沉思。[viii]其融合出来的结果至少有两种特点。首先,它对思想史的开放态度,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文坛上是少见的,因爲后者往往患着媚外贬外两极化的政治倾向。其次,它对华语作家和非华语作家挑战,能否把自己的语言场域拓宽。说钱钟书把外国思想介绍到中国,未免看轻了他的贡献,因爲他拓展的评论和文学实践相成的场域,是限于欧洲语系语言的作家和批评家所达不到的。
在《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中,钱钟书有时也使用消极的写法来表示世界主义精神。比如,他反覆地谴责人类患近视眼。在钱钟书看来,这特别是文人的职业病。在《释文盲》中,他把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的世界观明喻成“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或者一隻苍蝇“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因爲眼珠太小,看不出世界多麽广大。在《上帝的梦》中,上帝像作家一般的虚荣心,使他看不出他的创作(男人和女人)的真相,后来被他们背叛。在《灵感》中,一位瑞典的汉语音韵专家不愿意为其它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委员解读一本(被翻译成世界语的)中文小説,因爲他们问的“是汉文的意义,那不属于我的研究範围。至于汉文是否有意义,我在自己找到确切证据以前,也不感武断。”这位“支那学”者还“谦逊说自己还比不上获得本届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美国眼科专家,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的病。”《管锥编》的书名本身也重提这个“视野”的主题,并转爲自嘲。
钱钟书的文学世界主义不只能从文章的主题看出来,也可以从形象语言的使用看出来。譬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钱钟书最喜欢用明喻来把概念雕琢成器。钱钟书在《管锥编》也说:
説理明道而一意数喻者,所以防读者之囿于一喻而生执着也。星繁则月失明,连林则独树不奇,应接多则心眼活;纷至沓来,争妍竞秀,见异斯迁,因物以付,庶几过而勿留,运而无所积,流行而不滞,通多方而不守一偶矣。[ix]
以上的观察让我们发现钱钟书作品中的一种张力:一方面有形象语言的多面性,另一方面有取现实主义为前提的单一性真理。钱钟书在讨论诗的时候,进一步指出“诗中之博依繁喻…积渐而高,力久而入(cumulative,convergent)”。[x]这个观察恰好也能形容他的散文和小説。对此种游戏精神的极端诠释,是把钱钟书当作后现代主义作家来看待,说他通过指出语言和想法的相对性的效果,创造了一个浮动能指(floatingsignifiers)的领域。[xi]不过,钱钟书至多走到了后现代的边界上,并没有跨过去,因爲在玩弄语言的弹性,他其实重新证明了语言的价值。不管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係有多麽纤细,钱钟书明明知道:语言有意义,也有力量。
钱钟书固执要保持宏观的批评视野,特别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政治趋势的冷淡态度,证明他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文(看下一节的详细讨论)中,钱钟书说这本书不过表示个人的感受,但「冷屋随笔」(《写在人生边上》中四篇文章最早发表的系列)象徵的不仅是钱钟书在昆明的住宿寒冷,[xii]进而是“冷眼旁观”的批评理想,作者认爲它最好是从“边上”来实现的。钱钟书在《释文盲》说,人的一种特徵是人能够採取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人“能够把是非真僞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的确,他的守己安分和自制力,让他在二战的穷困和政治压力下完成这些创作,说不定也让他过滤掉了毛泽东时代的杂音,完成《管锥编》。
自我边缘化
《写在人生边上》的序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在其内我们可以发掘对钱式批评-文学实践的真知灼见。在序文中,钱钟书把人生比喻成“一部大书”,然后概括地讨论这部大书应该怎麽去“看”。他先与自以爲是权威的当权派(“书评家”)划清界限,然后为个人性的反映遣兴—比如,书页空白上写的感嘆号或者潦草的夹文。如此,钱钟书断言说,批评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标準来接近他的批评对象,也说他不必勉强地把个人意见塞进一篇连贯性的宏大敍述。他主张独立观察,否认一个批评家的批评必须是系统性的或者先后一致的。序中用蓄意清淡的、甚至言不由衷的口气,而这可能会让我们忽略掉这种批评论对钱钟书的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篇独立宣言。閲读能够引发新的心得,特别是“不慌不忙”的“浏览”。钱钟书的比喻,虽然等于把世界放在了两面书皮之间,其实它暗示人生中的矛盾和不合理现象不能以一个理论贯串起来。“人生一大部书”这比喻把对人生与文学的评论当作一个持续的对话,在书的空白上随便划拉几笔就能把文本的範围扩大。再者,这个比喻提倡对自由语言游戏的开放心态。他邀请读者不必太认真、接受文章中先后矛盾和不相入的地方、凑凑热閙。就像钱钟书在《论快乐》试图説服读者:“矛盾是智慧的代价。”
边缘性,是最早在《写在人生边上》中探颐索隐的主题,也是钱钟书和杨绛的文学生涯中的主旋律。像上面所述,《写在人生边上》的书名塬来是杨绛提出来的。半个世纪以后,当叁联书店正预备出版《钱钟书集》的时候,她再次提了这个主题,把钱钟书的其他评论文章收入文集,取名《人生边上的边上》。到了年,九十六嵗的杨绛写了一本对死亡和死后生活的书,取名《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该书名,杨绛在序里解释,一直搁在脑中,逼着她为他人不能替她回答的问题,写下自己的答案。
钱钟书虽然熟悉其他人的理论,就跟杨绛一样,他最终要靠自己的本事回答人生的大问题。在私人生活中和文章中,他从来不向人讨好。根据杨绛的回忆录《我们仨》(),钱钟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参加了他必须参加的会议,除此之外只管埋头做学问。夫妇亟执自己“不合群”,在晚年的时期宣告愿意过隐士一般的生活,只管读书,不要被外人所打扰,甚至对一位要求访问的学者写信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自我边缘化是钱钟书自给自足的思想空间,让自己的读书癖得到纵容。这等于说,钱钟书求知的场域,是在文学的开放世界,而不是社会的相对来讲比较封闭的环境。不管钱钟书自选的闭门谢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限制他的文学观,他的内向化暗示他不愿意受到他的时空的任何心理上的限制。
百科全书式的笑
钱钟书的散文和短篇小説中的动力之一,是一种像电流一般的笑声。就像《围城》一样,这些作品中有数不胜数的异想天开的警句、妙语、明喻以及语言笑话。比如,《人兽鬼》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在表面上,书名不过是把书中的主人公归于叁类东西。《上帝的梦》中的神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失望,后来使他们趋死。《猫》中的主猫公“淘气”,在敍述中神出鬼没地现身。《灵感》的主人公“作家”,无意中的文学自杀把自己变成鬼,下地狱以后要面对阎罗王般的“中国地产公司”的司长,然后经过出人意料的投胎过程。在《纪念》中,一位空军的飞行驾驶员与一位寂寞的家庭主妇发生关繫,他丧身以后,妇人只在肚子里留下他的“纪念”。这些故事的共同焦点是人生、死亡、转世,和復活—换一句话説,是人、兽、鬼叁类状态之间的不断来往。
不过,《人兽鬼》的书名也是模棱两可的,是钱钟书在合併叁类、使其间的界限模煳化。《上帝的梦》中的上帝“毕竟还保留人的脾气,”或者是,由于幼稚气太浓,他甚至是一个算不得人的婴儿;《猫》中的爱默,则反覆地被说像自己的家畜。钱钟书好像在暗示:每个人都叁份像人,七份像兽和鬼。或者,从作者在《上帝的梦》、《读「伊索寓言」》和《谈教训》中对进化论的轻视来看,“人兽鬼”一说,未必是对人类的煺化论。在钱钟书的作品中,读者越来越期待和欣赏这种有歧义的词句。与此同时,作者教我们小心,随时都可能会上他的当。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钱钟书喜欢玩弄语言形式逗笑逗思。比如,他的散文的结构,常常使用“需要”和“多余”的对比。在《写在人生边上》的第二篇文章《窗》中钱钟书写道,“门是住屋人的需要,窗却多少是一种奢侈。”在《説笑》中他指出,“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爲人类并不都需要笑。”“奢侈”这个贬义词的运用,有意哄骗读者以爲作者有意攻击奢侈,但是下文却是讚美“有余”的美学乐趣,类似于庄子所谓的“无用之用”。
这种颠倒手法,象徵钱钟书游戏般的逆流倾向,它本身是自我边缘化的一种表现。这些借题发挥的段落,操纵逻辑和常识、模仿正论。名家的宏论被断章取义而出、引语被错用得驴头不对马嘴。通过常识的颠覆,钱钟书把逻辑先解构下来、再重构成一个可辨认的但是自相矛盾的形式,进而让人体会到,语言的规律容易引向歧途。譬如,人的年龄与人类的年龄这两个似乎平行的概念,但是如果以同样一片逻辑去分析它们,可以达到很荒谬的效果,比如《读「伊索寓言」》里这连串主张:
把整个歷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慢慢的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歷史愈短;时代愈在后,它积的閲歷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祖父的老辈,上古叁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祇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
显然,钱钟书不仅要指出语言所导致的逻辑谬误而已,进而要对语言的漏洞,无孔不入地、乐嗬嗬地去戏弄、操纵、颠倒它的形式,直到荒诞的效果。
夏志清曾经大方地写道,“钱钟书创作的中心目的其实并非去揶揄知识分子及作家,而是要表现陷于绝境下的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的永恒戏剧。”[xiii]的确,不少小説的剧情显出这种广阔的视野,比如在《猫》中爱默、建侯和颐谷的复杂关係。不过,钱钟书并不以人身攻击为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猫》中的虚构的北平高等社交圈里,袁友春是林语堂(–)的替身。单看一个小片段,也可以体会到钱钟书人物漫画化的复杂性:
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认爲中国旧文明的代表,都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閒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团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是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麵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像在外囯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爲是中华风味。...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是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像鸦片瘾来,直打哈欠,又像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又说,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爲安眠药发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埋有副作用。
这种超出敍事主綫的精彩片段(setpiece)象徵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特殊谐嚯文体,叫做梅尼普讽刺体小説(Menippeansatire)。梅尼普讽刺取名于古希腊哲学家和犭儒(Cynic)梅尼普斯(Menippus;约公元前叁世纪),是一种欧洲古典文体。它与普通的讽刺体和长篇小説的不同,主要是在它视思辨能力为最高美德。虽然对该文体的定义不一,[xiv]它的主要特点包括:它混合几种散文体的书写手法,有时也插入诗;它表现一种博学的作风,同时常常嗤诋不及格者;它爱玩弄矛盾(paradox);以及它喜欢堆积、编单子等积聚东西的方法。弗莱(NorthropFrye)认爲小説家与梅尼普讽刺家的不同,在于前者“把恶愚视爲社会病,梅尼普讽刺家则把它们视爲理智方面的病。”因此,后者“所处理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心态(mentalattitudes)。”[xv]梅尼普讽刺家有两个相关的目的:第一是通过解剖与分析揭露他人思想的不足,第二是表现自己的超等智力。为此,他使用多种手法,其中比较招眼的就是,作者不断地、而且积极地卖弄学问。
就像很多梅尼普讽刺家一样,钱钟书的论説“立场”并非固定的,而且是一直在巡迴的,因此读者和对手很难把他定下来。W.ScottBlanchard说“梅尼普讽刺家,虽然往往是一个鸿博的作家,但他在哲人与反知识分子的偶像打破者两个角色之间侧身,这位贤人即是文学界最讨人喜欢的要命鬼。他的态度是...‘要不断地嘲笑制度的创造者。’”[xvi]钱钟书笑声中的解构主意因素见于他作品中的仿颂词(mocken白癜风应注意什么甲氧补骨脂素洗剂
转载请注明:http://www.ddnhj.com/wazz/870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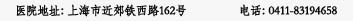
当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