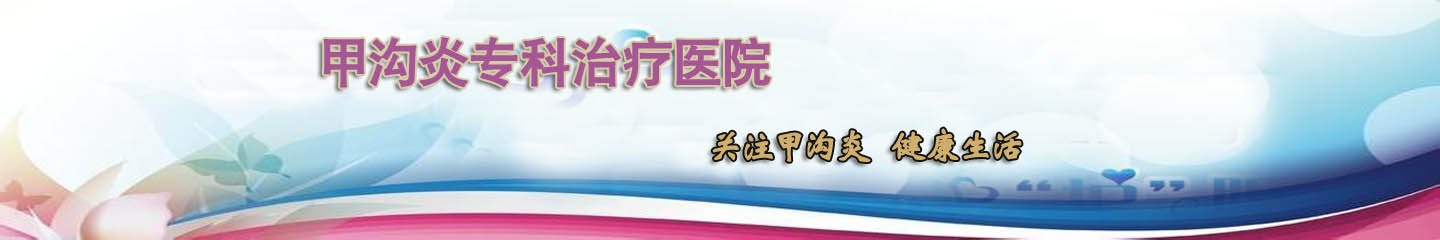杨东平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读莫兰复杂
导读
在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中,看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的《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此书是年在巴黎出版的,所思所想与我们在大疫中的感受几乎同步而高度共鸣,可见其思想的穿透力和理论的洞察力。莫兰的学术生涯,涉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最重要的主张,是面对错综复杂和日益不确定的世界,我们需要革新文明的范式,用“复杂性思维”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未来。
——杨东平
本文作者: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莫兰关于不确定性的思考
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后果,在造就了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埋下了毁坏这一文明的暗线。今天,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每一个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人口激增和贫困问题、核武器扩散和战争威胁、难民和移民潮、恐怖主义等等——无不是高度综合和复杂的。突袭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则是一个最新的警示:我们征服自然和争霸世界的雄心与我们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抗疫表面上反映的问题是公共卫生危机和防疫水平、社会治理和全球合作能力等;背后却是我们的知识观、方法论、世界观,是我们认知世界的眼光出了问题。
知识系统的迟滞和失序,早已被学者觉察。年,英国物理学家C.P.斯诺首先提出“两种文化”的命题,指人类文化被割裂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两者不仅互不相通,而且互相鄙视,难以对话。莫兰其实是延续了这一讨论。60年之后,情况究竟是改善了,还是更加糟糕了?
莫兰分析了科学的范式问题。尽管人类问题日益综合并且错综复杂,已经成为跨学科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和全球化的;但是自牛顿时代建立的教条仍然占统治地位,这就是以分析为主、还原论、线性因果关系、决定论等传统“科学方法”和思维范式。C.P.斯诺呼吁的是培养我们这个时代兼通文理的通才,但现实却是伴随知识激增、学科分化导致的“超级专业化”。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比例过大的各个学科的专家”,但知识系统却“愈来愈脱离人类的控制”,因为科学的范式总体上仍然是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整体性的问题被“像红肠一样切割开”,成为“超级专家”的盘中餐。
莫兰称超级的学科精神变成了一种“地主精神”,仿佛用排尿来标志地盘的狼群,禁止他人的进入。无限细分的微观研究,还原论的后果之一,是掩盖了整体的复杂性、实体的多维度性、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关系等等,因而往往失去了对复杂问题的总体性和根本性认知。
莫兰还敏锐地指出了还原论的另一个特性:把研究局限于可测定、可量化、可形式化的东西上。然而,现实的生命、活动大多数是不能被数学化和形式化的。我自己的感受,量化研究的泛滥,是用各种术语、概念、算法筑起专业化的高墙,使非专家完全看不懂;而研究的结论,有些与经验高度一致,完全不需要用那么“高深”的研究;有些是明显违背常识的,其余的那些发现和分析,则是令人将信将疑的,同类研究的结果也相差很大。海德格尔称迷信数量分析的“算术狂”“吞吃了计算的本质”,嚼碎了存在、性质和复杂性,超级专家丧失了设想整体性和根本性的能力,一个显例是经济学。在最具精确性、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经济学领域,不仅专家难以在经济预测上意见一致,其预测又常常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完全无力预测和防范如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因此成为“数学上最先进的和人文最落后的学科”。因为它拒绝面对复杂性,而是将经济活动简化再简化、定量再定量,因为它“不能思考无法量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类的热情和需要。”哈耶克因此说“没有一个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人可以成为大经济学家”;而且“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会变得有害无益,甚至构成一种真正的危险。”
▲埃德加·莫兰
特别令人受益的,是莫兰强烈地意识到知识激增、学科割裂和超级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化进程对公民的挑战,导致民主的大幅度倒退,“民主的亏损在不断增长。”社会的“高级种姓”和“技术特权集团”把日益增多的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处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对重大问题的垄断,剥夺了公民认知的权利、侵蚀了公民总体性和深度思维的能力。对当代战争的认识,可以形象地认识这种“民主的亏损”:过去我们可以利用插在地图上的小旗来跟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那么今天对战争的电脑计算、情景模拟、远程打击等等,已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了。最极端的是“原子武器完全剥夺了公民反思和控制它的可能性,”而被交由国家首领的个人决断。因此,他说,“政治愈是变成技术性的,民主的权能就愈是萎缩。”
文明范式的陈旧落后,致使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弱智”的。莫兰指出“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沙俄帝国中的苏维埃革命、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胜利、年德苏条约的戏剧性变化、法国的崩溃、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顽强抵抗,所有这些都是出乎意料的;直到年的意外事件——柏林墙的倒塌、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南斯拉夫战争。今天我们处于黑夜和浓雾之中,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结论是“知识既未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也未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我们面临的是随机性和偶然性、非线性、自发性、混沌等新特征,需要学会“在散布着确定性的岛屿与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没有历史的“规律”,没有被允诺的进步,我们手中并没有历史进步的遥控器。
疫情反思
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和防治,几乎是说明莫兰复杂性理论的鲜活案例。不同国家对突发疫情共同的迟钝、忽视、盲目和掉以轻心,各种手忙脚乱、应对无策,凸显的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困境。只能说人类是健忘的,我们太习惯了理性的、线性的、严格规划的、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沉浸在“岁月静好”的秩序感中,而对潜伏在身边的随机、突发的风险缺乏敏感和准备,也缺乏与病毒长期共生并存的生存智慧和技巧。许多人在预言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当世界陷入隔离、分裂、各行其是的混乱之时,只有无国籍无护照的病毒在继续全球化进程。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许多主观的、刚性的、静态的、曾经有效的管理失效了,陈旧的治理框架在动摇,有人发推文说“听到了梁柱噼啪作响的断裂声”。
政府处置的快速高效和顾此失彼,凸显了行政化的优势,也暴露了其功能割裂、信息不畅等固有弊端。因为大国疫情的防治,是高度综合复杂的问题:既包括防疫、隔离、救治、疫苗研发等医疗和公共卫生事务,需要整体性、专业性的社会动员和管控;也需要对经济活动、劳动就业、学校教育、居民日常生活、弱势群体救助等作出安排;需要有效的社会参与、基层的社区服务,需要充分的信息流通、报警、表达和宣泄的机制,也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国际合作和建设性的大国外交。在收治和医疗、“封城”的社会管理、资源供给和配置、信息控制等几个主要因素中,不同国家的不同模式,值得日后的深入总结和评价。
专家系统的公信力同样在被贬损之中。各说各话的专家意见,无法兑现的疫情预测,夹带私货的用药方案,往往令人摇头。医学研究虽然已深入到分子、基因的层面,在微观上应该说是极其科学化了;但医学研究的整体范式,仍然是分离的和割裂的。病患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其年龄、基础性疾病、身体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治疗方案理应是各不相同的。分析的还是综合的、微观还是宏观、治病还是治人,正是中西医之争的一个文化背景。
在高度专业化-科学化的研究过程中,人的价值迷失并非夸张。只要想想走火入魔的“基因编辑婴儿”案(主犯贺筑奎已入刑),即可明白“纯粹的”科学研究在反人性上走得有多远。这也正是人工投放病毒之类“妖言”泛滥的一个背景——除了自媒体时代众声喧哗、蛊惑人心的言论、众多毁灭世界的阴谋论灾难片的影响;也是由于公众对科学的伦理、科学家的信任感降到了某个低点。
至于“民主的退化”,只要想一想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那么多致力于恶化大国关系、喊打喊杀的“战狼式”言论,对温和理性的方方的深仇大恨,就令人有不知今夕之感。人们在思考为什么尽享改革开放的好处、并无文革经验的一代,会变得如此偏狭极端,暴戾乖张?他们不惜一战的叫嚣,有对于民族命运和国家根本利益的理性考量吗?他们对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最丑恶、破坏最为惨烈的灾难,有真实的感觉吗?
有人提出“思想病毒”的问题,在这次疫情中,其危害并不比生物病毒更小。众多
转载请注明:http://www.ddnhj.com/wahl/1058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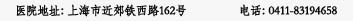
当前时间: